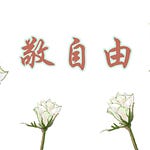2020年9月,封城中的我從超市囤糧回家後,發現朋友轉給我一個小影片:
《囤起糧食,我就想到外婆的野菜王國》1
咦?這名字怎麼看起來像是我寫的某篇文章?
懷著好奇心點開,看完後直接驚呆,這就是我故事的影片啊!可看來看去,怎麼總感覺哪裡不對,彷彿在大街上遇到一個做了整容手術的老熟人,看見對方的新面貌,忍不住要端詳哪裡和記憶中不對。片中女主溫柔俏麗,就連口音,也帶著一種動畫片專有的可愛腔,糯糯的,嗲嗲的,朋友把她和我野蠻的形象對比一番,留了四個字:「萬分震驚」。算起來,這部小影片,是我的故事第一次被人用視聽方式講述,那麼它到底要講甚麼呢?
在電影世界,編劇的首要任務是一句話總結劇情。電影預告,簡介,海報都必須清楚地呈現這句話。這對總覺得一句話說不清事情的人來說,簡直是場酷刑。
如果把這部影片用一句話總結,就是封城囤糧讓我想起了外婆的野菜食譜。影片呈現的是新冠流行背景下身在法國的某遊子在封城中回憶起外婆的野菜食譜,在回溯外婆智慧時,她對家的深切思念和母女三代人的依戀之情也浮現出來。如果說作品是時代產兒,那麼這部小影片的內容其實非常符合2020年9月中國的主流宣傳價值觀,它出現時,正是世界因病毒陷入停擺,而中國以其舉國封國之力,樹立起世界危機中抗疫「優等生」的形象,成為了疫情中世界「安全島」,當月北京還在召開全國抗疫表彰大會的時刻。外婆的菜譜,外婆解決糧食危機的方法,似乎成為了傳統智慧在世界危機中取之不盡的隱喻,也描繪出那些因為疫情封鎖不能回國的海外遊民的家國之思。這個呈現角度,放在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和文藝宣傳中,其實是非常討巧的。
但是,我在2020年寫的原文:《囤起糧食,我終於理解了外婆》,如果也用一句話總結,它的核心完全不同。這篇文章寫的是中國1960大饑荒的歷史創傷如何通過食物和社會危機顯現並且代際傳承。外婆之所以有野菜食譜,是因為從1950年代末期,中共領導階層的一系列政治決策錯誤,導致了全國餓死三千萬人的大饑荒悲劇。當年在沒有任何食物的情況下,面對快要餓死的孩子和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我的母親,年輕時代養尊處優的外婆必須為母則剛,想盡一切辦法求得食物,極盡所能地利用各種食材,導致食物變成一種心理創傷,而習慣性囤糧的行為則變成創傷後應激反應。她的後半生都在歷史創傷留下的陰影中受苦。而這種應激反應在新冠這場全面社會危機中,從我的母親處爆發,又傳遞在即使身在異國的我身上,形成了共振。外婆的食譜,不是智慧的源泉,更不是回憶裡閃閃發光的溫情,它是傷痛的標誌,是被迫換了個笑臉的歷史創傷的證明。
也就是說,小影片迴避了文章主線——大饑荒歷史創傷的代際傳承,她繞著道走,在苦難中提煉出了懷舊小清新力量和當時大環境下非常應景的中國海外難民和遊民的家國之思。
讀到這裡也許你會覺得我相當不知好歹,作為一名小作者,一篇不到萬字的文章被大平台製作成小動畫片,又不用自己花錢費工夫,多麼開心和幸運的一件事,居然不知感恩。其實以上只是對這部影片和我自己文章關係的回顧和評論。如果連作為作者的我自己都不講述,不記錄,不好好面對自己作品的微型歷史,那麼有一天,這段歷史不但會被記性不好的我遺忘,還有可能會被竄改(雖然不知甚麼人會care😄)。而時代歷史,正是所有個人歷史的總和。也是最近,我才深刻意識到,面對新冠時代的全球悲劇,我們現在的記錄和反思遠遠不夠便已經開始遺忘和竄改,這種遺忘,已經從個人微型歷史開始。
但是,當我從冷酷無情的文藝評論角度退後,回歸這部小影片產出的時代背景和中國的言論狀況時,我又看到了另一種景象:其實我應該感謝當時決定把它製作成影片的中國非虛構寫作平台——網易人間的原編輯們。對我這個無名小作者不到一萬字的短篇作品,他們能夠花時間,功夫,花錢認真對待,在追求快錢的新媒體世界,以慢工出細活的精神,做了個有趣的,但無法帶來快速流量和直接變現的視覺實驗。在那麼多不可能碰紅線,只展現人生藝術的飲食故事中,他們完全可以有更安全的影片題材選擇。在大饑荒這段歷史講述空間相當逼仄,不知哪方面就會出事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拐著彎地去講,多方面展現和推廣這篇文章,把讀者引向原文。並且在這篇文章的出版過程中,陪我一起面對意識形態審查,以強硬的態度和出版社博弈,留下一個又一個本不應該被刪除的句子。如果你手中碰巧有我的書《好吃的故事》,如果你讀到了這篇故事,請記得,它差點不可能出現。這篇文章涉及到大饑荒歷史部分的每一個字,都經歷了被沉潭,被打撈,再沉潭,再打撈的過程,最後修改成為了你看到的樣子。
而這篇有關囤糧文章的命運,不論是何種講述,誰人講述,何嘗不是一段需要被我自己認真記錄下來的,極權社會言論命運的微觀歷史。高壓之下,中國有情懷的編輯們,在步步都可能出錯的環境下,活得謹慎,憋屈,但他們仍在努力用好自己手裡僅有的空間,盡可能地去擴大言論自由的疆域。其實關於中國的言論自由狀況,我常常在法國被問到,人們的理解非黑即白,要麼自由,要麼死,極權社會就是全民被監控,人人監視人人,完全沒有任何說話的自由。在這裡我並沒有替中國糟糕的言論環境辯護的意思,但是我想說的是,當我們認識中國社會時,不要忘記黑白之外,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灰色地帶,灰色偏白還是偏黑,則取決於每一個身在其中的人。這部小影片對原文文本的改編和重新講述,其實也可以算作灰色地帶的一部分。同一個故事,在中國,根據政治社會環境,可白可黑,看你怎麼講,看你敢怎麼講,看你能怎麼講,看他們規定你怎麼講,而講述的尺度,時刻可以根據外部環境和人際關係發生變化。
但是我們不該忘記,哪怕是同一個故事用不同方式講述,都會製造出完全不同的效果,產生不同的世界。它們傳遞給世界的,其實是不同講述方式背後的價值觀念以及能量。正因為有這部影片作為遠因,我開始對文本,視覺藝術載體,社會和故事流傳的關係非常感興趣,所以《魚書》開闢了《魚影》這個欄目,和大家一起學習影視知識,在文字之外,用另一種方式把故事再講一遍,至少從記錄我個人寫作歷史和我自己的故事開始。
我不知道這種講述能走多遠,但我相信它雖微不足道,然而自有其意義。
至少,你的閱讀和觀看,就是意義。
探險依舊,我仍在路上。
What does the soul truly want is a story.
― 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也以此文祝賀網易《人間》原編輯部全員移民,今日在愛奇藝推出非虛構寫作欄目《身邊》。和《魚影》的推出莫名奇妙撞在同一天。當然,如果以後你們還能在中國見到我文章的話,那不出意外,她不在《人間》,而在你《身邊》陰魂不散。
此文部分節選自《好吃的故事》續篇《被槍斃的西瓜》。《被槍斃的西瓜》是《好吃的故事》在出版期間經歷的意識形態審查故事,將在《魚書》連載,想看更多,請訂閱支持《魚書》。
此影片為網易人間出品,出處链接:https://m.163.com/exclusive/video/VKMMKG3LO.html?clickfrom=channel2016_exclusive_all_newslist